本文是一篇法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处理贿赂犯罪时,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罪刑关系是否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是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的罪刑规范。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腐败问题一直存在,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多次就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作出修改和完善。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因行贿而被处罚的案例,延至明代,立法体系上曾对行贿行为进行国明确的区分并加重其量刑处罚。清末时期,我国初步确立了近代刑法意义上的行贿犯罪的立法体系,在借鉴西方近代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又保留了一定封建特色[3]。民国时期,对行贿犯罪首次将比较明确的罚金刑引入到立法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于1952年颁布了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律,是我国刑事立法对行贿罪的最早规定。1979年颁布的《刑法》,在第八章渎职罪中直接规定了行贿罪,但对于行贿罪的概念和构成并没有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直至1988年弥补了这一立法空白[4]。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有关行贿罪的刑罚体系更为完善,进一步细化了行贿刑罚,对刑罚和量刑情节也都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5]。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立法上对行贿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加大其刑罚惩治力度,2015年通过的刑法第九部修正案重新修订了行贿罪,包括增设罚金刑、从严适用从宽处罚以及限定三种减免处罚情形等。然而对行贿惩处失之于宽的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实践中,同期受贿案件和行贿案件的查处数量上仍有很大的差距[6]。“行贿罪与受贿罪案件数的比例大致在1:3,有的年份达到1:4甚至有时比例会更高,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适用缓免刑的比例也已达到了一半以上。可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实现,现实与法律修改初衷还有差距,打击行贿行为仍然是目前亟需不断重击且长期坚持的事情。”

第二节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行贿犯罪这一经典刑法问题经过诸多学者多年相互探讨、理论交锋和在司法实践中的不断适用与总结,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相当丰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也在同步修订,目前现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就是在不断吸纳和参考学者的理论成果和司法实务中总结出的实践成果。刑法学界对行贿犯罪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修正其构成要件、完善其量刑标准、司法实务的适用、厘清可与之竞合的罪名等展开。
一方面,最为广大学者所喜论的就是对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设置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不正当利益”的理解和适用相对不明确,关于“不正当利益”内涵和标准的界定,学术界争议颇多。关于“不正当利益”的存在非法利益说、职务违反说和不应得利益说等很多理论观点,如“赵秉志教授曾撰文并专门谈到了“非法利益”,这是关于“不正当利益”性质的一种看法,他认为“非法利益”才是真正的“不正当利益”,与司法解释中所说为追求个人合利益而行贿的行为不是真正的行贿罪要处罚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②“车浩在其文章中说到行贿行为人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违背职务的行为为行贿行为人谋取某种利益,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这个行为的方式不管是作为或者不作为再所不问。”③对“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也存在着“保留论”、“废除论”这两种观点。李少平支持“废除论”,“因为在“事后酬谢”行为中由于行贿人在事前没有有意交付财物,仅以事后表达感激之情给付财物,不应当认定为行贿。”①“保留论”认为,“废除论”的观点难以区分行贿犯罪与违规赠送礼品礼金问题的重要政策界限[1]。迄今为止,学界对行贿犯罪中“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的讨论还十分激烈。
第二章行贿犯罪的内涵解析
第一节行贿犯罪的概述
行贿现象的形成及演变具备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深入剖析行贿罪的根本属性与含义,对于探讨行贿罪并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极其关键的实践价值。
一、行贿犯罪的本质
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也就是说,要想探究行贿犯罪的本质,就要找到行贿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贿赂犯罪和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都被刑法理论讨论过,唯独行贿罪的保护法益没有被独立讨论过[2]。关于贿赂罪的法益和受贿罪的,在日本普遍认知有四种学说:不可收买性说、纯粹性说、综合说和信赖保护说。我国有学者在保护法益上对行贿罪进行了讨论,结果与受贿罪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由于贿赂罪包括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结合种种研究现状,可以得出行贿罪的保护法益也存在上述四种学说的对立与区别[3]。由于受贿、行贿同属贿赂犯罪,因此在讨论行贿罪的保护法益必须注重贿赂罪的基础学说。同时,也需注重行贿罪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的区别。行贿罪与受贿罪在犯罪构成上成立条件不同,行贿犯罪法定须“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受贿犯罪则分情况,索取财物的行为定罪不须这一要件,说明二者的保护法益不尽相同[4]。
贿赂犯罪的基础学说中有关保护法益,一是源于罗马法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罗马法认为收受贿赂是为将来做出的职务行为这一行为构成受贿罪,原因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就有可能危害公务行为的公正性,就历史悠久的针对法官的受贿罪来说,《十二铜表法》做如下规定:“审判者或者裁定者在审理之际,收受一方为换取影响裁定结果而支付的金钱代价或其他利益的,应被判决极刑。”据此,《尤里乌斯法》认为只要是收受一方为换取影响职务行为而支付的金钱代价或其他利益既可成立贿赂罪,而不追究该职务行为是否违反职务正当性。二是源于日耳曼法的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说。
第二节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的内涵解析
1997年现行刑法和通过的12个刑法修正案自施行以来,对多次调整行贿犯罪。织紧织密“反腐”法网,推动反腐败制度不断细化。刑法上对行贿犯罪进一步明确规定的趋势,是对国家刑事政策的有效吸收,也为这次《刑法修正案(十二)》的修正提供了正当理由。
一、充分贯彻了“受贿行贿一起查”这一刑事政策
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行贿犯罪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行贿不禁、受贿不止,现实生活中行贿犯罪不断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态势,这种现象引来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刑事政策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起先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开始转变贿赂犯罪的治理策略,从“打击行贿服务于查处受贿”到“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二十大要求“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同年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最高检在2022年印发了《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进一步健全完善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提起行贿便会想起受贿,这一对合犯注定了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二者的打击力度也应当不相上下,刑法学界不尽然也存在着反对“受贿行贿一起查”甚至主张废除行贿罪的观点,但都经不起推敲和反驳。”①从国际法视野,中国国作为联合国的缔约国,也应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得到启发,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是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应然要求。
第四章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立法走向
第一节演进的理由
此次修订具有必要性,旨在解决法定刑罚的失衡问题,并防止利用单位名义逃避刑责。此外,此次立法修订还体现了其价值,即对刑事政策的回应,以及对情节在刑罚调节中作用的重视。
一、修改的必要性
为了有效地治理和打击行贿犯罪问题,进一步充分发挥了刑法在全面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中的关键作用。具体来说,立法修正成为遏制和预防行贿犯罪的重要法律工具,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法律制裁,形成强大的震慑力,使潜在的行贿者不敢轻易触犯法律。同时,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堵塞法律漏洞,提高行贿犯罪的法律风险和成本,从而使得行贿者在法律框架内难以实施犯罪行为,达到不能腐的效果。
(一)法定刑失衡
刑事立法特别重视体系性的结构布局,这不仅体现在新旧两部刑法典的核心特征上,也是未来刑法再法典化所追求的完善路径。过去,刑法在对某些具体犯罪的罪刑设定上显得较为随意,缺乏协调性。以行贿犯罪的法定刑为例,最高法定刑分为有期徒刑10年、5年、3年,导致刑罚立场显得混乱,缺乏一致性。然而,本次修正加强了贪贿犯罪的罪刑配置之间的协调性。
罪刑均衡是实现刑罚公正的必要条件,同时体现了刑法平等原则的核心价值。刑罚的性质应当直接反映犯罪的性质,这就要求刑罚与犯罪的严重性相匹配。刑罚的轻重可以视为刑罚与社会需求之间动态关系的体现,在刑罚的种类选择、量刑配置等方面的反映”。因此,刑种的选择和刑度的设定都应当彰显出均衡性。修正案作为近年来刑事立法修订的主要途径,其修订内容本身也在努力实现体系上的协调。换言之,通过刑法修正案的修订,刑法得以在体系层面上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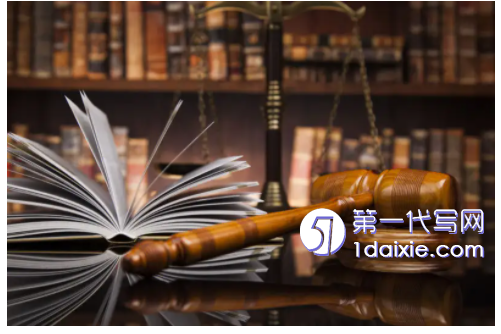
结论
司法实践已经表明,对行贿者的宽容过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根除腐败的根源,相反,这种过度的宽容可能会助长更多的行贿者毫无顾忌地对公职人员进行拉拢和腐蚀。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出台旨在加强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其价值取向是值得肯定的。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实施,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行贿犯罪的数量和惩治力度上将实现显著提升,有助于形成强大的震慑力,遏制行贿犯罪的蔓延势头。
处理贿赂犯罪时,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罪刑关系是否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是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的罪刑规范。这需要我们在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时,既要考虑到形式正义,也要兼顾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确保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即任何犯罪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同时也要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匹配。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确保定罪量刑的公平和公正,从而使得对腐败犯罪的治理不仅在法律上站得住脚,而且在社会上也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确保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略)
